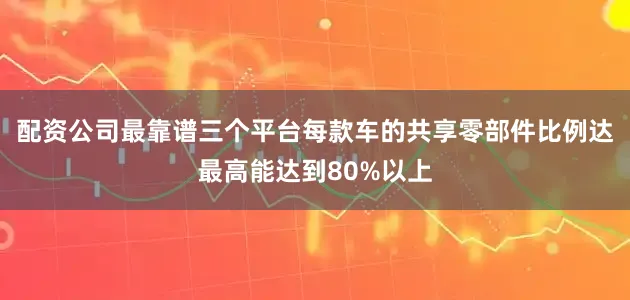今日7月13日
狼虎谷血战,黄巢的失败是如何影响唐末历史走向? 文|潇湘倦客末日黄昏公元884年7月13日,泰山九顶山南麓,此地古称“狼虎谷”,因猛兽出没而名,如今却回荡着凄厉的喊杀声。密林间,一支残军正负隅顽抗,追兵已逼至谷口,哀嚎与刀鸣,交织成一曲无章之挽歌。
黄巢就困在这片乱石嶙峋的山地中。昔日自号“冲天大将军”,率百万大军席卷中原,令大唐帝国为之一震。此刻却面容苍老,甲胄残破,身边只剩寥寥数人。关于他的死法,后世传说不一:有说他自刎于乱军之中,有说旧部林言斩其首以献唐军,换得一纸赦免。
展开剩余89%史实难明,但结局已定:一个曾在血与火中扶摇直上的草莽英雄,终归掩埋于荒山野岭。夕阳映照下的尸体,没有丝毫帝王气象,只是一具溃败之人残破的躯壳。群山寂静,帝国梦尽,狼虎谷的黄昏也就此凝固为一段无法回首的历史暗影。
盐商之子时间倒回到十二年前,乾符二年(875年)深秋,山东曹州冤句县。一位名叫黄巢的年轻人从长安传回的榜单中,再一次找不到自己的名字。他沉默许久,忽地将手中毛笔掷向窗外,笔杆撞在墙上,碎成两节。
他已考了五次进士,却始终不得录。黄巢不是普通的寒门子弟,他出身于本地盐商之家,家中有钱,有势,还有私人武装——在地方上掌握一支护运盐队,晚唐乱世当中这只武装力量足以震慑盗匪。然而,这一切在门阀当道的科举制度面前,毫无用处。他的科举之梦终究不过是笑谈,他被钉死在士族设定的天花板之下。
这一年的冬天,他没有再去准备春闱,而是在家族亲族的聚会上,第一次提出起事之意。他并非最早揭竿者,王仙芝早在长垣举旗,而后黄巢很快响应,与堂兄黄揆、族弟黄恩邺等八人密谋举兵。
他说:“我若起事,不为一己功名,而为天下不平。”
这话后来流传甚广。是心声,还是托词?已不可考。但正是在这场由制度边缘人点燃的烈火中,大唐的命运,悄然偏离了原有的轨迹。
草莽军团黄巢起兵之初,手下不过百余人,都是族亲旧友和盐队武装。但随着队伍自山东南下,沿途击破曹县、阳翟、郏城等八县,兵锋直指汝州。一支杂牌军,就这样滚雪球般,规模逐渐膨胀,变成了横扫中原的乱世洪流。
他麾下聚集的人,是那个年代最边缘的群体。他们没有理想,也无从谈信仰。里面有破产农户、逃荒灾民、落第举人、盗盐者、流亡军卒,各怀心思,却有一个共同点:对当下的社会秩序彻底失望。
有人曾记述黄巢军初兴时,入村安民、守纪分粮。但这不过维持了短短几月。随着战线延伸、军队人数暴涨,而粮草枯竭,队伍很快就暴露出最本质的问题,掠夺成了他唯一获取供给的方式。
黄巢曾写过一首诗,《不第后赋菊》:“待到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后百花杀。”很多人记住了这句张扬的豪言,却忽略了这首诗出自一位未能入仕、终以兵乱改命的士子之手。
他曾渴望以文入世,但终究靠武力闯关。他的军队,不是理想塑成的利剑,而是制度缝隙中淤积已久的苦水,被强行引爆成洪。
含元殿下的幻梦中和元年(公元881年)冬,长安城风声鹤唳,曾经象征帝国无上威严的含元殿,迎来了新的主人。更令人震动的是入城时的景象。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开门投降,黄巢大军顺利入城。
百万铁骑涌入这座帝国心脏,出人意料地,城内并未发生大规模劫掠。黄巢下令封仓赈粮,禁止扰民,甚至亲自巡视坊市,派兵维持秩序。黄巢军士对惶惑的长安百姓宣告:“黄王起兵,本为百姓,非如李氏不爱汝曹,汝曹但安居无恐!”他甚至向贫民散发财物。
有人不解,有人敬畏,还有人开始窃窃私语:这位草莽出身的将军,是否真想坐稳龙椅?
仅仅几日后,广明元年十一月十六(公元881年1月16日),黄巢在含元殿登基,改元“金统”,国号“大齐”。百官仓促就位,旧唐制度悉数照搬。登基那天,长安并不喧嚣,甚至有些沉默。百姓围观新皇,眼神里既有期待,也有本能的不信任。
此时,那个落第的盐贩之子,似乎真的渴望建立起一套公平的社会秩序。他尝试着设立新的官僚体系。可惜这些努力无法改变这只队伍的流寇机制。
他依靠的是流民乱军,他任命的官吏也多为战将子弟或亲信,这些人难以胜任治理国家的重任。导致财赋征收混乱,地方豪强趁机坐大,可以说,黄巢建立的是军事政权的躯壳,依靠武力生存,没有支撑它长久存在的制度和社会基础。这种“流寇政权”,无论多么风光一时,终难逃被根深蒂固的旧秩序反扑的结局。
那一刻,他或许真以为自己能成为第二个汉高祖。但历史是冷峻地,他并未真正拥有一个国家,只是暂时占据了一座空城而已。
暴政从“洗城”开始长安,易手不过数月。
次年春,唐僖宗避难蜀地,收拢藩镇援兵,自剑南、河东、岭南调军反攻,官军兵临咸阳。大齐军防守不利,长安再度陷落。新主未稳,旧主未远,城市再次沦为沙场。只是这一次,进城的不是黄巢,而是唐军。
谁也没有想到,复入的唐军并未施行“王师仁政”。相反,他们对长安进行了赤裸裸的报复:民居焚毁,街市掠洗,妇孺被辱。目睹旧朝官军暴行的百姓,一时间竟对黄巢政权生出复杂情绪——“那时虽苦,至少安生。”
唐军反扑长安成为黄巢心理转折的引线。
很快黄巢收拢败军自霸上反攻,再次攻克长安。此时的黄巢,已无心维持入城之初的仁政形象。在他看来,唐军能力快速反扑长安必定是长安的百姓暗中相助,是“通敌叛逆”,他决意清算。狂怒之下,他下达了惨绝人寰的“洗城”令。
据《旧唐书》载:长安城内“流血成川,谓之血川。”
昔日“本为百姓”的承诺,在权力的猜忌与报复的疯狂面前碎如齑粉。春明门等要冲之地,血河三日不绝,繁华帝都沦为修罗屠场。
黄巢“洗城”令,洗刷的不只是长安的街巷,更是他曾经维系的“起义合法性”。他亲手斩断了起义之初“为百姓而起”的誓言。从那一刻起,大齐政权不再是乱世的希望。
流寇本性暴政一旦开始,便难有尽头。黄巢的军队如同巨大的蝗群,所过之处,“百姓净尽,赤地千里”。他们掠夺一切可食之物,却从未建立稳固的后方,更无恢复生产、赢得民心的长远之策。大齐政权本质上仍是流寇,只有破坏,毫无建设。
致命的背叛接踵而至。中和二年(882年)九月,黄巢倚重的大将朱温,在同州前线与唐将王重荣交战中败北,眼见大势已去的朱温,悍然倒戈降唐。朱温被唐廷赐名“朱全忠”,后来成为终结大唐的枭雄。朱温的叛变如同釜底抽薪,极大动摇了齐军根基。原本凝聚在黄巢旗帜下的多支部队开始动摇,忠诚度骤降。
内失民心,外有强敌,盟友叛离,黄巢的大齐帝国迅速崩塌。中和四年(884年),唐廷借朱温之力,联合沙陀族和各地割据势力,对大齐展开三面夹击。黄巢四面受敌,军队在连续战斗中日渐疲惫,兵员伤亡惨重,补给线被切断。在唐军与强悍的沙陀骑兵联合追击下,黄巢一路溃败东逃。曾经的百万雄师,此刻只剩下残兵败将。
黄巢最终倒在狼虎谷的血泊中,他的头颅被作为战利品呈递唐廷。清代学者聂剑光在《泰山道里记》中留下记载:“黄巢死于泰山……九顶山南有大冢,俗称黄巢墓。”九顶山南那座沉默的坟冢,与泰山永恒的巍峨形成刺眼的对比。
黄巢死了,当他却揭开了唐王朝覆亡的序幕。
朱温、李克用这些在他尸骸旁崛起的枭雄,最终完成了对帝国的肢解。他留下的,是一个被战火彻底掏空的中原,是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的惨状。其从子黄皓率残部流窜,号“浪荡军”,数年后在湖南被地方豪强剿灭,唐末这场席卷大半个帝国的农民战争才最终落幕。
尾声黄巢的失败,既是一场个人悲剧,也是一场制度与结构的惨烈碰撞。他曾揭竿而起,寄望以暴力撬动沉疴。然而,终究缺乏治国良策,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。
884年7月13日,黄昏时分,狼虎谷中残阳滴血,昔日的“冲天大将军”已成历史尘埃。而腐朽的大唐王朝虽得以苟延残喘,却已魂飞魄散。
参考文献:
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泰山道里记》(清代聂剑光著)
————☀本文完结☀————
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不错,
欢迎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、留言❤
更多内容请看🔻
聊聊“九品中正制”:魏晋的“拼爹”游戏,如何玩崩了一个王朝?
九品中正制:魏晋时期的‘拼爹’游戏,寒门子弟的千年之痛
图片来源网络,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
发布于:湖南省一直牛配资-配资查查-配资炒股网站-配资网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